生命价值的沟通:器官捐献中的文化困境(2)
其二,医家的察情而医。中国古代著名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不失人情论》中载:“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脏气之不同也。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10]李中梓用其切身经验告诫医家,医家应能在诊疗当中对病人心理进行揣摩分析,以便采取相应的行为疗法以取信于病家(而不仅仅是病人本身),一方面求得更好的疗效,另一方面避免纠纷。在现代医疗环境中,越来越现代化的就诊环境、纷繁复杂的就医程序、医疗合同中的法律专业术语、手术室门栏上亮起的“手术中”的警示等,都在有意无意中削弱了医患之间的社会互动。我们不得不反思如何冲破现代化的种种、如何冲破医学的专业化让患者,让患者家属等体会到医生的一颗仁爱之心。以器官捐献为例,当捐献者被推进手术室后,家属往往只能在冰冷的走廊上等待,对于他们而言死亡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却是在他们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捐献工作,除了关注医学的救命天职,也不该忽视对捐献者及其家属的人文关怀。器官捐献有其特殊性,虽然移植医生面对的是已经逝去的生命,但其不应忘记对捐献者家属的察情。
4.2以多元信息交流为基础的社会互动
中国古代的医者主要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医,众所周知中医诊疗讲究望、闻、问、切,其中的问诊蕴含了医患之间丰富的社会互动。中医问诊的信息不仅包含着病人的基本病情,还囊括了病人的生活喜好、社会关系、心理状况等众多内容。《难经·六十一难》载:“问而知之者,问其所欲五味,以知其病所起所在也。”[11]。《丹溪心法》载: “凡治病,必先问平日饮食起居何如。”[11]《医学准绳六要》载: “凡诊病,必先问所看何人……次问得病之日, 受病之原,及饮食胃气如何,曾服何药,夜寐何如,膈间有无胀闷痛处……诊病必问所欲何味,所嗜何物,或纵酒,或斋素,喜酸则知肝虚,喜甘则知脾弱。”[11]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当代的医生就不问了呢,问的内容就单一了呢?其实不然,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医生如何摆脱医学术语的束缚,用普通患者能够理解的方式来“问”,来沟通,来互动。在这一点上,或许古代温情脉脉、穿着大褂长衫的医者更能给我们以古老的智慧启迪。而在当代,以器官移植中的捐献为例,如果器官捐献中的协调员在与死者家属沟通过程中一味只谈献赠问题,其他问题毫不涉及的时候会让死者家属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正如上文中提到的,许多ICU医生不愿意涉及到器官捐献工作,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担心患者还在治疗过程中,跟患者谈捐献问题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猜忌。据笔者了解到在J市医院有通过设立器官捐献宣传栏的方式使家属主动来咨询捐献相关事宜的情况。由此可见,如何避免刻意只谈捐献问题,如何在一种多元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家属意愿,让家属享有绝对的尊重和自主权十分重要。
4.3以“较单一”媒介交往为基础的社会互动
中国古代医者与患者间的沟通媒介受历史的局限性往往表现出比较单一的情形,通常以面对面的交往为主。这样的社会互动方式,医患之间互动的时空范围相对有限,互动的对象也是相对固定和熟悉的,其优势是医患之间往往十分相熟,处于共同的或交互的社会关系格局当中,从而为医患间便利的沟通互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现代医疗面临着跨时空信息传播的无限可能,大大拓展了医患互动的时空范围和方式,但无论世界如何瞬息万变,都离不开医患之间的相互理解,只有相互理解了才能有效互动。在古代单一的媒介交往为我们创造了较易相互理解的大环境,因为我们彼此熟悉。而未来世界,或许会因为科学技术而使医患相距千里毫不了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无论是医生亦或患者即便相隔千里毫不知情,但是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我们有着共同的人伦价值理念,我们有着共同的生死疾病观念,这就是我们互动的基础,不会因媒介而改变的人文基础。以器官捐献为例,捐献者及其家属要面对器官获取医院、移植医院、红十字会等数家机构,与此同时还要面对OPO负责人、移植医生、志愿者、协调员等不同的人员,而这些人员不同的身份、不同的隶属都有可能给家属带来紧张感,因为他们不了解他们面对的是谁,以及不同的机构在捐献这件事情上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起着怎样的作用。由此可见,我们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在器官捐献工作中应如何做好分工,而当前我们最欠缺的则是在移植技术与普通民众医学文化观念之间架起沟通桥梁的这一角色扮演者,在器官移植的紧张过程中我们当然无法苛求移植医生如传统中医问诊那般,所以在当前实践中有了协调员、志愿者等新的角色参与,但接下来的工作应是结合地域特色明确协调员、志愿者及相关人员的角色和功能,以不至于在捐献过程中因身份角色的混乱而给捐献者及其家属造成误导与紧张感。
4.4以中国传统礼法规范为共同基础的社会互动模式
社会学家李安宅[12]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写道:“中国的‘礼’字,好像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等……既包括日常所需要的物件(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超自然等关系的节文),又包括制度与态度。”在古代社会中,社会分工程度还不高,医者所遵循的诊疗规范以及医疗习俗往往也是符合人们日常所遵循的一套仪礼法律规范的。
以诊金的支付为例,《红楼梦》中提到的一个关于医疗的细节或许可以作为考察古代医患互动的一个参照。贾宝玉的丫鬟晴雯病了,请来一位大夫胡君荣诊治,尽管贾宝玉对他开的药方并不认可,但既然请来了,诊金还是要付的。给多少呢?按照当时的行情,老嬷嬷建议:“少了不好,看来得一两银子,才是我们这样门户的礼。”宝玉道:“王大夫来了,给他多少?”婆子笑道:“王大夫和张大夫每常来了,也并没个给钱的,不过每年四节一个趸儿送礼,那是一定的年例。”[13]又如康熙辛卯(1711年),李光地门人陈汝楫忽患重疾,群医束手,最后被青浦何氏始祖何王模之父、何氏奉贤支名医何炫治愈。陈汝楫感激之余,认为“赠人以金,不若赠人以言”,遂请其师李光地撰文表示感谢。李光地以前在维扬的时候,也曾找何炫看过病,因此爽快地答应,撰《赠自宗何子序》,回顾了自己和弟子请何炫诊病的经历,并以“良医良相”之说来赞誉何炫的高明医术和高尚医德[14]。
由此可见无论是诊金的支付也好,还是病家对医家表达感激的礼物馈赠,这一互动关系互动规则都遵循了中国人最传统的人情文化,风俗习惯。阎云翔[6]7在《礼物的流动》中写道:“礼物馈赠是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社会交换方式之一……研究礼物交换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理解和诠释既定社会中不同文化规则及社会关系结构的途径。”以诊金的支付以及礼物的馈赠来看,并非我们通常理解的仅仅只包含一种类似契约关系的互动,而更深层次的是包含了中国人的金钱观、人情观、交往礼节等等复杂的情感。这也就是为何在处理器官捐赠当中,如未能合理处理好人道关怀的问题会让病患或病患家属有一种“买卖”了器官的情感体验,而并非是基于人情、人道主义关爱的情怀。怎样去拿捏器官移植中涉及的“无偿”、“补偿”、“买卖”这三者之间微妙而敏感的差异,或许医学本身并不能给出答案,而需要对中国本体之中的文化传统进行深入了解才能拿捏到位,做到合法、合情、合礼。
总之,中国古代医患之间也可以说是医学与文化之间,为何不存在较大的隔阂,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医患的文化价值观念是相似的,他们处在相同社会文化、社会观念以及社会规范当中,因此医学与文化并不存在较大的矛盾之处。而自近代医学技术迅猛发展以来,医学的标准与文化的标准越走越远,于是医学与文化的矛盾开始日益凸显。当前我们急需要做的是如何通过医患之间的互动来减少医学与文化上的鸿沟,如何寻求当代医学与普通民众互动中共同的文化理念。落脚到器官捐献问题则是如何寻求移植技术与本体民众医疗观念、生命观的沟通与互融。正如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克劳福德(P.Craw-ford)所提出的需要一个“更具包容性、更加开放和更面向应用的学科,以包括那些被医学人文边缘化的贡献”[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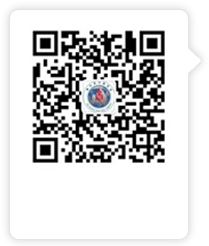





最新评论
点击刷新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