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的“五大红卫兵领袖”后来都是什么结局
他们在“文革”期间曾叱咤风云,独领风骚,是不可一世的学生“领袖”。他们的名字,对于从那个年代走过的人来说,也是耳熟能详。当他们为过去的行为付出了惨痛代价后,如今,又身在何处?

五大红卫兵领袖
乱世狂女聂元梓
聂元梓因为一张大字报,成为“文革”风云人物。她先是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继而在1966年8月18日上午毛主席接见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时,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聂元梓和军师们策划抢了三个“头功”。第一是“揪叛徒”。在聂元梓的授意下,他们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为叛徒。这些老同志相继被捕入狱。其中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被折磨致死。第二是诬陷朱德委员长.聂元梓召集手下干将,炮制了《历史的伪造者、反党野心家——再评〈朱德将军传〉》等三篇反动文章,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在国内外造成恶劣影响。第三是贴出全国第一张公开炮打邓小平总书记的大字报,诬陷邓小平同志是“全国第二号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其同时,聂还加紧了对邓小平子女的迫害。邓朴方被剥夺了人身自由和申辩的权利,开除党籍,刑讯逼供。邓朴方采取了当时惟一可行的方式来表示他的愤慨和不平。他从楼上纵身一跳……

1969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不久的聂元梓被发配到江西省鲤鱼洲北大分校农场劳动。她往北京写信,第二年夏天得以回京治病。1971年初,聂元梓被隔离审查,限制行动自由。1973年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1975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锒铛入狱。
聂元梓的个人生活很不幸,1959年,38岁时同第一个丈夫离异,主要是迫于政治上的压力,1966年同第二个丈夫结合,又是淡而无味的婚姻。“文革”时,她违心地领着红卫兵去抄丈夫的家。抄家后,丈夫前妻的儿子找到北大来论理,她还躲着不敢见,并暗地里指使红卫兵:“他们不是好人,轰出去。”从此,她和第二个丈夫脱离了关系。聂元梓在73岁那年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page]
地派“女杰”谭厚兰
谭厚兰曾是北京的大学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大学的造反派曾分为“天派”、“地派”,谭厚兰与王大宾结成“地派”。一天,康生把谭厚兰找去,让她去山东曲阜孔庙造反。谭厚兰带领井冈山的200余人,在曲阜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从1966年11月9日至12月7日,他们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的国宝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这场浩劫是全国“破四旧”运动中损失最为惨重的。

谭厚兰
1968年7月28日凌晨,谭厚兰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他们光搞武斗,不搞斗、批、改。次日,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师大,谭厚兰被抛在一边。1968年10月,她作为大学生,被分配到北京军区某部农场劳动。1970年6月,清查“5?16分子”运动开始,谭厚兰被调回北师大隔离审查,交代问题,从此失去了自由。1978年4月,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了谭厚兰。在监狱中,她痛心自悔,用自己的揭发交代,证实了自己的痛切之言。1982年6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做出了对谭厚兰免于起诉的决定。1981年,谭厚兰检查出患有宫颈癌,被保外就医。9月,又允许她回老家湘潭治病。1982年11月,谭厚兰静静地在痛悔中走完了人生的最后路程。这年,她才45岁,没有结婚。
几度风雨王大宾
1966年大学毕业前夕,王大宾狂热地投入到那场席卷全国的“造反运动”中,拉起一支庞大的队伍,并很快被中央文革小组相中,成为当时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的“地派头目”。1968年毛主席关于红卫兵小将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发表后,这位已任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政委兼司令、首都红卫兵三司副司令、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政法组副组长的王大宾,被分配到成都探矿机械厂工作。

王大宾
1971年,王大宾因“516”问题被押回北京地质学院隔离审查,并被开除了党籍。1978年,他又以反革命罪被捕,一直关押在武汉第一看守所。1983年,王大宾获释出狱返回成都。1985年秋,在有关部门的关照下,王大宾又回到了成都探矿机械厂搞钎具,每月工资69元。
1973年,王大宾在接受审查期间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他的女朋友闻讯从成都赶到武汉,为他熬药送饭。他们于同年底结婚。第二年,添了个女儿。1983年,王大宾的妻子调回原籍深圳,王大宾却因故调不去,双方协议离婚。1987年夏季,有人给他介绍了都江堰市妇幼保健站的医生刘素芬。初次见面那天,王大宾首先送上一份别致的“礼物”——自己被关押受审的材料。刘素芬比王大宾小8岁,是共产党员。一年后,他们在刘素芬的单位宿舍结婚。
王大宾后来曾任都江堰市都信凿岩钎具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兼任中国钢协钎具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岩石破碎学会常务理事。他的公司生产的拳头产品已出口中国香港、东南亚和澳大利亚。
[page]
天派“领袖”韩爱晶
“文革”开始后,韩爱晶在去国防科委“请愿”静坐的28个昼夜中,空前活跃而坚定,一跃成为名噪一时的北航“红旗”战斗队的“总勤务员”(即总司令的代名词)。

韩爱晶 右1
1967年7月9日,在北航的一间教室里,韩爱晶写了自己历史上最肮脏的一笔。这个小型“审斗会”审斗的是功勋卓着的老帅彭德怀。当时彭总任西南局建委第三副主任,三线副总指挥。韩爱晶非法强行揪回彭老总,声称“审斗会”要“刺刀见红”。会前,北京卫戍区的同志奉命向韩爱晶宣布了周总理“不准打、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斗、不准开万人以上斗争大会”的五项指示,韩爱晶却声称“周总理的指示已经过时”,带头对彭老总逼供和殴打。他们逼迫彭老总在他们写着“反对毛主席”罪名的纸条上签字并写“认罪书”,刚直不阿的彭老总据理驳斥、拒绝签字。韩爱晶恼羞成怒,先后7次将彭老总打倒在地。使彭老总前额被打破,左右两侧第五、十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一个星期后,北航又召开了数万人的“批斗大会”,不顾彭老总的严重伤病,会上对彭老总搞“喷气式”,会后又挂牌游斗,并再次毒打彭老总,连陪斗的张闻天同志头部也被打成血肿。
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授意下,韩爱晶率人诬陷和企图打倒徐向前,绑架、迫害张平化、叶飞、徐海东等人……同时,他们在北航院内设立了名为“隔离室”的监狱18处,先后立案审查了465人,其中170人受到非法关押,造成20余人非正常死亡。1979年,公安机关正式逮捕了韩爱晶。1983年6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造反“司令”蒯大富
1968年6月21日蒯大富在清华提出要赶走工作组。结果,清华大学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了多次反蒯斗争,蒯大富被开除团籍。7月18日,形势急转,毛泽东指示:“不要工作组,要革命师生自己来搞。”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很快,蒯大富成为清华井冈山的头目,人称蒯司令。

1967年1月6日,蒯大富组织井冈山兵团干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智擒王光美”。他们诈称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压断了腿,需要截肢,把刘少奇和王光美骗到医院,然后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4月,在蒯大富的主持下,清华大学召开了批斗王光美的大会,彭真等人也被押来陪斗。从1968年5月29日到7月27日,在蒯大富领导下,清华大学武斗一直没有停息,这就是着名的“清华百日大武斗”。武斗中死伤多人。
7月27日,工宣队进入清华,宣传制止武斗。蒯大富决定以武力抵抗,不让工人进校。造反派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工宣队袭击,5名工人被打死,731人受伤。毛泽东震怒了。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点了蒯大富的名。会后,五大学生“领袖”回到学校放下武器、拆除工事。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了一名电解工。
1970年,清查“5·16分子”,蒯大富是重点清查对象。11月初,他被押回清华受审。1973年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劳动。1978年4月19日,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蒯大富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回到青铜峡铝厂。1992年,他和妻子来到了山东省蓬莱市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蒯大富被任命为总公司总工程师。
XLW
[page]
亲历者自述:我在文革中遇到的可怕荒唐事
文革札记:一件可怕的荒唐事
那是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这把火已经烧了快两年了,北京中学校园里的“革命”早已落潮,大字报、大批判、激烈的派仗,渐行渐远,再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了。“复课闹革命”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流产。平日校园里,除了开饭的时间,几乎见不到有人在走动。很多同学根本不来学校,有些人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一面。那时住校的同学不多,小猫三两只,学校开始恢复昔日的宁静。不同的是,失去读书声的校园,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落寂与荒凉的感觉。

说起来,年轻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纪,虽说无所事事,整日也闲不住。那时,我与朋友郑君“盘踞”在校园偏僻的角落,昔日的理发室成了我们的窝居,在里面当起逍遥派,夜伏昼出,无拘无束,很是惬意。自打文革开始,理发师傅早已去向无踪,住在那里最大的好处是安静,室内有水有电,洗漱煮食十分方便。

那些日子里,闲了,我们或是闭门读书,或是外出游玩,无线电、半导体也算是另类的“路线斗争”;饿了,或是去食堂打饭,或是用电炉煮面条稀饭;馋了,两人凑点零钱去小饭馆搓一顿。通常是在周末回趟家,与父母打个照面,顺便带回一些米面油盐。那时,在大学工作的父母也身处文革的激流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根本顾不上子女。作为没有书读的中学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算是十年动乱里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了。
[page]
记得有一天,是军宣队还是当时管理学校的什么人跑来叫我去办公室,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核实。来人一脸严肃,似乎真有大事要发生。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紧随而去。
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低声交谈,神情肃穆,看装束打扮就知道是外地来京的外调人员。文革时期,流行外调,全国各地,屁大点事就会派人出去调查,反正坐火车不要钱,顺便游山玩水,到处逛逛,公私兼顾,何乐不为?

“你是高二×班的同学?”我还没有落座,已经有人开始发问了。
“听说去年你去过江西?”
“去年我们学校去过江西的人多了,还有两位同学惨死在南昌城外的乱枪之下。有什么事吗?”我颇有些警惕地反问。

“这我们知道。你与廖×林是同班同学吗?”
“没错,去年4月,我正是与廖一起从北京出发去的江西。”我暗自琢磨,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讲述一下你们去江西的具体情况?”听对方口气比较委婉,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page]
那时的外调五花八门:追查历史的,核实现行的,有的没的,七大姑八大姨,老死不相往来的,都要给你查个人仰马翻。外调人员也是鱼龙混杂,看菜下饭,嘴脸不同:对行政级别高又没有“被打倒”的,他们小心翼翼,笑脸相陪,唯恐得罪;对黑五类,走资派,他们居高临下,声色俱厉,显尽威风。
从他们的表现,你可以判断出自己的处境。必须说明的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人性很难得,最不缺乏就是打手与恶棍。有时,这些家伙往往比主子更加可恶,更加难缠。所以,那时不管什么人,面对外调人员时总是要加倍提防,避免给自己或是亲朋好友招惹麻烦。

既然人家客气,咱也主动配合。况且时隔一年,记忆很清晰,我便从出发开始讲起:
1967年4月,文革进入最为诡谲的时期,全国各地革委会相继成立,各派大联合却又大打出手。开始棍棒石块,继而真刀真枪,你攻我防,热闹非凡。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太平,大学在打,中学在斗。武斗死人的消息此起彼伏,早已不再是新闻。同班同学廖×林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关心和参与学校里的文革运动,经常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听说江西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危急,也想顺便去革命圣地井冈山看看、逛逛。或许认为时局动荡,出远门有个伴儿好些,于是他便找到了我。两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一拍即合,说走就走。

我们从北京站乘南下的火车,经郑州、武汉,在株洲换车,4月下旬到了南昌。那时的南昌气氛相当紧张,一派退守,一派围城,扬言“农村包围城市”,即将“血洗南昌”。城里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闭户,街道上行人稀少,不时有各类武装人员乘卡车或是列队通过,带有高音喇叭的广播车来回穿梭,呼吁人们“誓死保卫南昌”,随时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夜晚,城里城外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大战在即,处处风声鹤泪。
[page]
我俩刚到,人生地不熟,经常在空荡的大街上闲逛,也曾到南昌起义纪念馆里寻找枪支。怎知,晚来一步,能用的早被人抢光了,只好将出土的,已经拉不开栓的残破手枪,包上块红绸布,别在腰里给自己壮胆。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搞笑。
没过几天,我在江西医学院遇到了北京商学院的老张,他当时是南昌城里的风云人物。他介绍我到南昌铁路局造反派组织办的《铁道风雷报》里当摄影记者。据说是要拍下一些武斗场面与伤亡人员的照片,上交中央领导,反映江西文革的危机状况。

满怀革命壮志的我,十分敬业地接受了这份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行的廖君不以为然,他依旧坚持要去吉安,上井冈山,我俩就此分道扬镳。随后几天,听说他在吉安遇险,被对立派抓捕。那时的小道消息五花八门满天飞,真假难辨,听说也就听说,根本无法核实,加上那阵子我确实很忙,整天挎着相机,开着吉普车到处跑,没时间细想,也就没往心里去。
“这就对了!”我说到这里,有人插话。

“廖×林同学在吉安生米镇被捕后遇害。前一阵,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经群众举报,凶手落网。残害他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讲述作案经过,指认作案现场,我们这次来北京就是要落实这件命案。”
我听了大吃一惊,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page]
“怎么会搞错?廖和其他几位遇难人员的遗体已经被挖掘出来了,这是当场拍摄的照片。”有人把几张照片推到我的面前。
“这怎么可能,上个月我还见到了廖×林。他家住在北大蔚秀园,离学校很近,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核实。”我看也没看一眼照片,胸有成竹地说。
接着,我把廖后来给我讲述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

廖是乘船去的吉安。由于天气闷热,傍晚他在甲板上睡着了。怎知,这艘木船突然遭到对立派船只的攻击,两船相撞,廖和一些人落水了。随后,他们被对方用长竹竿打捞上岸,经过审讯,关押起来。半夜时,有听懂当地方言的人悄悄告诉他们,对方打算将他们处死,为自己一方死难的人员报仇。
大家一听,慌了神。那阵子,江西武斗十分激烈,枪来炮往,死伤惨重,最后双方都杀红了眼。常常出现亲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虏报仇雪恨的惨剧。我作为“战地记者”,亲眼见到并拍下了被捆绑在树上枪杀或是用刺刀捅死的血肉模糊的尸体。

说起来,人真是奇怪的动物,第一次见到这样血腥的场景,我浑身发抖,胆战心惊。后来见多了,习以为常。竟敢独自一人,打着电筒,在冰冻的冷藏车厢里,为成堆的死人逐个拍照。战场上的死者,大多肢体残缺,嘴斜眼歪,面目狰狞。当时的我,还不到20岁,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却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与恐怖。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言归正传。当时,廖和一起被关押的人听到死亡的消息,害怕过后,决计拼死一搏。午夜,他们趁看守人员松懈时,撬开后窗,逃了出来。他们慌不择路,在漆黑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拼命奔跑,终于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没想到,一个晚上,没吃没喝,竟然从江西跑到了福建,才算松了一口气。可见,求生的欲望,真的可以产生常人无法解释的巨大能量。后来,廖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page]
望着桌上的照片,我们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位稀里糊涂顶着廖×林的名字死去的人是谁?怎么会发生这样可怕的荒唐事?对于我的同学廖×林来说,真真切切地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实属万幸。
可是,那位“冒名顶替”的死者呢?他也是父母生,父母养,活生生的一条生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残害了。十年文革,血迹斑斑,罄竹难书,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全民族的浩劫。中华大地,上上下下,几乎无人可以幸免。这场动乱,无论过去多少年,至少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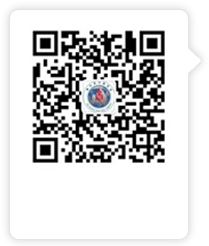





最新评论
点击刷新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