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头发说到辜鸿铭、林语堂:“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
从古到今,头发之重要——用新学问来解释——乃因为是符号(文化的以至于政治、经济的符号),由于在头顶上,这符号亦比较别处为重要,虽其实不过人弄的把戏,与头发本身无涉的。所以鲁迅说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不但一点儿不错,恐怕又不仅是在论头发的二重性。兴许在那头发后面,还有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哩。有人遂了理想,有人遭了痛苦,尽管实在有点儿犯不上。
*文章节选自《回响的世纪风铃》(吴方 著 三联书店2018-8)。
电影《建党伟业》剧照,辜鸿铭与蔡元培
菊花插得满头归
由头发说到辜鸿铭、林语堂
文 | 吴方
《鲁迅全集》第一卷《头发的故事》,有句对白:“老兄,你可知道头发是我们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未免匪夷所思。头发不就是头发吗?脑袋上长出些纤维状的物质,或直或曲或粗或细或红或白或黄或黑,都不算异事,人们大可心安理得。除了早早“谢顶”或遭了“鬼剃头”的,要自己发愁投医,但此种人毕竟不多。至于人为什么要长头发,则颇难考证。人从猴子进化来,无用的尾巴已渐渐退化了。头发也几无用场,其功能却不萎缩,反于人有许多的名堂,想是因为头发乃于头顶上盘踞的缘故,上者尊下者卑,人体也不外“势利”如是。又,正因为没什么要紧的用,便不妨生出许多花样来,似乎人类个性于兹也可见一斑了。眼下,虽然我常为能剪个低档头而觉不便,但世上究竟以头发为宝者居多,秀发如云,发式亦即时式。摩登女士在头发上变出的花样,一般人说不大清,反正美发廊、护发美发产品之兴旺发达,大赚其钱,总归系于一发之间。感谢上帝安排——没有头发,该有多少人如丧考妣!至少,不以花样博览论,头发的整饬光洁度若较差,在高朋满座的风雅地方,总要埋汰几分,有落伍之嫌。
现代人的头发观,比较讲究也比较实际,比起过去的景况,自然开通多了。孔夫子云:“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后来辜鸿铭又说,“微曾文正,吾其剪发短衣矣”。很有些把头发的安排或服装的打点看得如安身立命一般要紧。可到后来,是披发是剪发,各由其便,“左衽”短衣的流行,也已司空见惯。倒也未见亡国灭种、道德沦丧。
好像怎么都行。可历史上又不如其然。从古到今,头发之重要——用新学问来解释——乃因为是符号(文化的以至于政治、经济的符号),由于在头顶上,这符号亦比较别处为重要,虽其实不过人弄的把戏,与头发本身无涉的。比如,和尚剃头是出家的标志,几世纪前欧洲男子戴假发是华贵的标志,清末“二毛子”之,有“洋毛子”“归纳法”“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男的“平头”、女的“刷子”,是“革命造反”的标志,而“牛鬼蛇神”发之被“髡”(如有“阴阳头”之发明),昭示“反动”之凿凿,等等。
欧洲男子戴假发是华贵的标志
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 Boucher﹞作品
所以鲁迅说头发是中国人的宝贝和冤家,不但一点儿不错,恐怕又不仅是在论头发的二重性。兴许在那头发后面,还有哲学、历史学、心理学哩。有人遂了理想,有人遭了痛苦,尽管实在有点儿犯不上。
冯骥才作小说《三寸金莲》,由器悟道,说女人的小脚里头,兴许就藏着一部中国历史,也未可知。关于头发或者男人头上的辫子,可打些折扣——若没有头发如何收拾这码事,中国历史诚然会少些冲突、热闹。
为头发而煞有介事或倒霉难受,以明、清两季为最。明季满族人来了,入主天下,不能置头发于不讲,非有“前剃后辫”的规矩不可,连唐宋文人那种“散发弄扁舟”的份儿也不准了。斧钺来讲道理,国人的辫子便拖定了。这给人的印象颇深。所以鲁迅后来说:“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到辫子在国情里笃定了,可还不能让头发平静。鲁迅又说,想不到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及至辛亥革命的前后,辫子的去留更成大是大非的矛盾。好在前贤们终于毕其功于一役,谢天谢地,革命将辫子变作古董,使我辈有脑后轻松的幸福。不过那时也不容易,因为斗争尚在胜负未明之际,游离在剪与不剪之间,也大有人在,他们免不了和剪“猪尾巴”的执行者大捉迷藏,或者练上一段百米赛跑。“二狗子,你的辫子还没剪啊?”“我告诉你说,不能留光头啊!好多人在传说‘宣统还朝,秃子开瓢’哇!”
留也痛快,不留也痛快,唯在留与不留之间者,虽然暧昧,也最有滋味:说是不好吧,其实可进可退;说是好吧,又怕有不虞之毁。这就需要智慧了——大约聪明的办法是盘起来,堆在顶上,不妨算是“咸与维新”兼“保存国粹”,也算“未庄模式”,可盘可放,随其所宜而适也。诚然是个不坏的法子。至于阿 Q盘了辫子却终至被枪毙,原是另外有因。而曾经万分英断的赵秀才终于因剪辫而号啕,那是不巧碰到了“不好的革命党”。总之,这盘、放原理在解决历史之“头发主题”方面,够得上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许仍积淀在心理上,时时给已经无辫的后人以影响。
辫子与辜鸿铭
时代真是进步了,变化的证据当然能在头发上找到。这不仅是指男人由必须拖辫到应该去辫,毋宁说,好在大多数可免了这份罪过,而愿意拖的也不妨还拖。总之,发型的问题归到个人的事。“头发一律”怕是与专制思想有关。我们虽说不喜欢留“猪尾巴”,但也不必去管别人的头发。民国以后,当皇帝也剪了头发时,蓄辫的也还有,其中有位辜鸿铭,在这方面还要做处士横议,至死不渝,在封建遗老中,算是最怪的一位了。
辜鸿铭之古怪——如不合潮流、守旧僵化、特立独行、桀骜不驯——大约与常人常情别于三途:一、身世浪漫传奇;二、思想、情感、行为的守旧执一;三、逆境中有一套精神胜利法。
先说第一桩。若是沐礼教世泽在传统中熏过来的人,要做孤臣遗老也还不怪,辜鸿铭却在格外。他是生在马来亚的华侨,其母为西洋人,从十岁起即去英国受系统教育,获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又游学欧洲,在巴黎、莱比锡等处大学获得十余项学位,可说西化透彻。但他愿意回来寻根、做事,而且一回来就扎根不走了,不能不说他对中国有特别的感情和认识。爱国爱到骨子里去,他爱中国的一切,从典章制度、哲学艺术,直到官员的朝服、女人的裹脚布。由西化到中化,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大概因濡染之深吧,与一般的留洋学生不同,他偏爱同洋人“较劲儿”。据说,有一回在英国乘巴士,遇见一帮趾高气扬的洋佬,洋佬露出瞧他不起的架势。辜鸿铭不动声色掏出一份报纸来看。洋佬们一看,个个笑得五官挪位:“看看这个大老土,连英文都不懂,还要看报!你瞧他把报纸都拿倒了!”辜鸿铭等他们笑罢,也不慌不忙,用流利的英语说道:“英文这玩意儿太简单,不倒过来看,还真是没什么意思!”
辜氏回国后,长袍马褂、瓜皮小帽,头发也皈依了辫子,娶中国式的一妻一妾,先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幕僚,后为清廷外务部官员,再后为北大教授。一九一六年蔡元培长北大,聘辜氏讲英国文学。在北大这块新文化园地,拖着辫子讲英国诗,是殊难想象的奇观,但也正见出蔡元培主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了不起处。蔡氏当年的声明说:“我聘用教员以其个人的学问、造诣为原则,在校授课以无悖于思想自由为界限 ……本校教员中如有脑曳长辫而持复辟论者,如果他所讲授的在英国文学的领域之内而无涉及政治,本校亦没有排斥干涉的理由。”蔡氏的道理可能还在于:如果容量太小的话,排斥异己,今天有排斥这个的理由,那么明天便有排斥那个的理由,学术的封闭也便假“理由”而行。辜鸿铭对此大概有知遇之感,所以当五四运动起来时,他便要和蔡元培同进退。其实,蔡是革命党,辜氏倒也敢说:“蔡元培和我,是现在中国仅存的两个好人,我不跟他同进退,中国的好人不就要各自陷入孤掌难鸣的绝境了吗?”别人问他“好人”之说如何解释,他答:“好人就是有原则!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而跑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到现在还是保皇,这种人什么地方有第三个?你告诉我!”
辜鸿铭
一九二八年,辜鸿铭在风雨飘摇中死去,他的信念、希望只能殉葬了事,被人渐忘。不过,由于他的译笔,《论语》《中庸》被介绍到西方去,加上他的西文著作的影响,名声在国外似也不小,连托尔斯泰、勃兰兑斯都很看重的。在东西文化交流这一方面应承认他有功劳,像他那样的中西文造诣,世上真是不多。他死后,有位外国作家勃朗特夫人曾对他的英文诗大加赞赏,感慨说:“辜鸿铭死了,能写中国诗的欧洲人却还没有出生!”
续说辜鸿铭与辫子
比较一下辜鸿铭的拖辫子与赵秀才式的“盘放党”,可能前者要好一点儿。好处在直率、不虚伪。至于他在各方面反对变革,倡言守旧,则不免多为强词夺理。像他为纳妾辩护时的理由——“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若别人说“一个碗里放两个调羹准得磕碰”,又如何呢?至于颂国粹、骂新文化,似乎迂阔,其实多在怪僻、多在自以为是,与人逆着来。他书写苏东坡的句子给搞复辟的张勋:
荷叶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擎雨盖指官帽子,傲霜枝当然是指两人同气相求的辫子了。爱辫子是个象征,爱清廷他以为即是爱国,其实他爱的是自己的理解,爱自己所喜欢的价值观念、思维和生活方式。其言其行,无不表现其爱的情结之深。
不过不如此也便不是辜鸿铭。承认这“怪”有它供参照的意义,不如此亦不成其为历史——历史总不是一种声音构成的。比如他抨击一知半解、食洋不化的陋习,讲过一则挺“损”的故事:
有一段时间,中国沿海及内地瘟疫流行,死了很多人。国内医生个个束手无策,最后不得不向西方国家求援,重金礼聘一位名叫“鬼放得狗屎”的专家渡海东来,考察一番。鬼放得狗屎先生到了中国,马不停蹄游走,详细观察,最后提出一份报告说:“贵国所流行的疫症,其实并不疑难,只是狗放屁所引起的。因为狗这种东西体性偏凉,不能乱吃杂七杂八的食物。在我们欧美各国,狗所吃乃是专家调配处理的狗食,所以全都健康强壮。而贵国狗所吃的却是不经选择的残渣剩菜,长久下来,消化不良,五脏六腑中郁结的秽气又不能下通,积变为毒,由其口出,这便是引起瘟疫的毒气了!总而言之,贵国的瘟疫百病,皆是由于‘狗屁不通’所引起的。 ”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此外,这老头儿还有许多指弹时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言论。《读书》杂志某期上有篇《怪文人辜鸿铭》,记了不少,可以复按。该文还提到有位温源宁先生概括辜氏的狂怪为天生要反潮流,跟时尚拗,所以便闹成一个很矛盾的形象:“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这是怎样的一种人格心理结构?不过,假如我们听到有人说“我是公仆,但一切都要我说了算”时,也并不一定很奇怪吧。
这个问题可以留给社会心理学家或历史心理学家来研究。
精神胜利法
关于精神胜利法,也许是辜鸿铭现象中更值得研究的部分。与阿 Q不一样,阿 Q善以柔克刚,被人打了,便说反正“儿子打老子”,圆圈画不圆,便说“孙子才画得圆”。辜氏另一路。第一,在遇到中西比较这种问题时,强调精神,不强调物质,总是说我们的精神文明好,西方讲物质文明出了问题(至于西方有无精神文明他不管)。不论如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以小人之道谋国,虽强不久,以君子之道治国,虽弱不亡”。第二,他有自己的是非观,同别人的是非观拧着,利用事物都有长短的特点,专以此之长制彼之短。第三,除了讲自己的一面之理外,对问题不大认真讨论,常常出之以幽默来搅和,所以多少能以智取胜,不像阿 Q那般“我们先前阔多了”的拙论。你看,他主张纳妾,别人反问他为何女人不可以多招夫,他只答:当然不可,你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碗,哪里见过一个茶碗配四个茶壶!问题似乎便解决了。据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他说:“听说你留学欧美,精通西学,难道不知道孔教能行于数千年前,不能行于十九世纪之今日吗?它已经是古董了!”辜鸿铭反问他:
数学家教人加减乘除,数千年前是三三得九,数千年后还是三三得九,难道还会三三得八吗?不过阁下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啦,这十九世纪的数学是改良了,刚才我们说三三得九也有不确之处,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向洋人借款,三三得九却七折八扣变成了三三得七,到了还钱时,三三得九却连本带利还了个三三得十一!嘿,我倒真是不识时务,落伍得很!
有的难题,让他一幽默,避实就虚,似乎就“化解”了。老辜两片嘴,有东方朔遗风。所以他虽然越活越背时,却还不乏良好感觉,比阿 Q强,端赖于精神胜利法。
续说精神胜利法
“你有千般道理,我有一定之规”,这虽然是精神胜利法的“基本法”,但正如事物均有发生发展的过程,精神胜利法也不免要在坚持中发展。怎么看?是否只有贬到劣根性上去,原也不一定。因为人对自己对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都还有些不可捉摸的地方,虽然好多学问,包括自然科学、哲学、文学都在研究人,也未能研究到很透。想了很多,还得承认,科学尚无法把人类个性化成方程式。所以现代的医生也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不能测算的因素:有的病人,如按逻辑推断,实在是应该死的,结果却不曾死,大概由于人有不同的反应力量。换句话说,精神胜利法也不妨是这种反应能力的一种存在形式。至于反应得好不好,合适不合适,一时也还不易论定。照林语堂的说法,证券交易所之不免成为投机事业,就是这个缘故。“当很多人想卖出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买进,当很多人想买进的时候,便有一些人想卖出。这里就有人类的弹力和不可捉摸的因素。当然,卖出的人总当那个买进的人是傻子,而那买进的人也以为卖出的人是傻子。”到底谁是傻子?常言道,世事须看开些,有点儿消极的意思,倒也未必就是没出息的消极。看得最开的是庄子。庄子的老婆死了,鼓盆而歌。惠施见了不以为然:你不哭也就罢了,这也太过分了!庄子回答:其实开始我也挺难过的,后来想,她原来是个“无”,由气而形而生而死,真像四季变化一样,很自然的事,我若老是嗷嗷地哭,不是太不开通了吗?对尘世生死的琢磨与看透,会培植起一种人类的喜剧意识以及用精神解脱来战胜现实的意向。怀有这种意向的人在生活中就不会太“执”,有点儿游戏感,或者说洒脱。于是,在对历史、人生的诙谐解释中,产生了幽默的风格。
假如一杯咖啡或一支香烟对于激烈的争论有缓和作用,假如我读某作家的作品感到有点儿亲切是因为他不拿“架子”,那么来点儿幽默感也不坏。幽默发展了精神胜利法的艺术境界。
当然,人们并不把油滑、做作也当幽默看。据说,幽默的特性在于微妙的常识、智慧、哲学的轻逸性和思想的简朴性,它逃避复杂和严肃。我还觉得,它往往无可奈何,是在玩世不恭中表现对玩世不恭的歉疚。说是由聪明入糊涂难,其实倒是看得比较透的。有位古人提到这问题:比如问世间极认真的事是什么,曰“做官”。极虚幻的事是什么,曰“做戏”。他说可能并不对。要说,做戏才是真实的,戏子因为做戏,得以养活父母妻儿,他的真实似乎就在于知道人生不过是一个剧场,而顶冠束带装模作样的官家,竟不知道这也不过是“拿定一戏场戏目:戏本戏腔,至五脏六腑全为戏用”,其实才是个真戏子哩!
人的心理结构中介入幽默这东西,近于装个阀门,原也不在于要解决现实的问题。人生往往太沉重,而幽默的语言活动、心理效应,也不过给人些清凉之味,不幽默,也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正如我们有时觉得阿 Q主义不好,有时又觉得在一定情况下还不能不且“阿 Q”一下才行。像下述的情况,还真不知是否有些苦趣呢!
一日,寒山谓拾得:“今有人侮我,冷笑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漠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林语堂
近世,在中西文化之间打交道的读书人中,林语堂是个典型的写家。他写作多而杂,台湾印的“林语堂经典名著”计二十余种。《生活的艺术》《吾土吾民》《苏东坡传》《京华烟云》等颇有影响。他独往独来,英文好,其作品多如海外游子归乡——出口转内销。在参加“国际大循环”方面,别人就不能和他比了。另外,他的经历也与他脚踏东西文化的写作特点若合符契,除了留学及短期做过教授、公务人员以外,长年以写作为生为乐,别的倒也没干成什么。自一九三六年出国海外漂泊,到一九六六年落叶归根,在台湾又住了十年后死去。也正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别人评论他的最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他也不怪,私许为契论,并以为开心不过的事,乃是把两千年前的老子与美国的汽车大王拉在一个房间内,让他们聊聊。他说,发掘一中一西之原始的思想而作根本比较,其兴味之浓,不亚于方城之戏,各欲猜度他人手上有什么牌,又如打完了四圈又四圈,没人知道最后输赢。
林语堂
林语堂与辜鸿铭都是向西方贩“国货”,且都有本位意识,但两人一道一儒,一实用一教条,一个讲享受人生之乐一个就认“冷猪肉”。辜氏执一,林氏执二。比如关于读书,林语堂就说他不喜欢二流作家,他要的是最高尚和最下流的(如民间船歌),因为喜其真实有活力。他推崇庄子、陶渊明的洒脱、淡泊,喜欢苏东坡、袁中郎的快乐、闲适。关于文化,他会辟一章谈论“肚子”——肚子美满了,一切也就美满了,“当饥饿时,人们不肯做工,兵士拒绝打仗,红歌女不愿唱歌,参议员停止辩论,甚至总统也不高兴统治国家了”。也会另辟一章谈“灵性”,说人的灵性并不在于追求合理性,而只是探索宇宙,恰如章鱼的触盘,亦如读小说,如果先已知道书中人物的未来动作和结局,小说便无一读的价值了。世间种种,不拘而谈,他大抵为率真、近人情作辩护,说是喜欢茶馆文化、肚子文化、眠床文化、流浪文化也都无不可。整个看,这当然不免偏颇,也不够深刻,可他自家先承认了不全面、不深刻——人生若都要全面、合理、深刻,且不说能否达到,达到了岂不也太乏味了吗?他以为,自己的兴趣只是知人生,兼要写人生,“不立志为著名的作家”也“怨恨成名,如果这名誉足以搅乱我现在生命之程序”,“我所要的只是不多的现金,使我能够到处漂泊,多得自由,多买书籍,多游名山——偕着几个好朋友去”。
像是“杂烩哲学”,如果林语堂有哲学的话。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这是林语堂关于人生配置的准科学公式。他还把这四样(简称“现、梦、幽、敏”)加减拼盘,来说明各民族的特质。并解释:有人说人生如一场梦,现实主义就说,一点也不错,且让我们在梦境里尽量过美好的生活吧,而幽默感又是在纠正人类膨胀的梦想和态度,敏感助成对人生的爱好,等等。总之,既实际又超脱,似乎给现世提供了一种林氏商标的甘草剂,至于管用不管用也没法质之于他,因为他又说自己并不是人类的医生,他不愿效法伟大的人物多管别人的事。
不过,他曾确实提倡幽默,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办过《宇宙风》《人间世》《论语》,屡遭批评,弄得苦恼。他以为幽默的好处,在于足以使理想主义者不至于把头碰在现实的墙壁上,看来也不外乎精神胜利法的法门。至于失败倘是没办法的事,那么,与其说那个说笑话者是残忍的、麻木的,还不如说人生是残忍麻木的了。
也许,林语堂所体验到的人生多半还是比较安逸平静的,所以极乐于引金圣叹的“不亦快哉”为同调。最后,他那要免除人们碰壁之厄的幽默,在中国也碰了壁。
来源:三联书店三联书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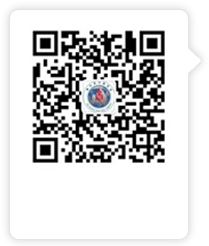





最新评论
点击刷新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