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老年痴呆以后,我们俩拌嘴,他每次都能精准敏捷的回怼
刚刚过去的那个秋天没有下过一滴雨,一直阳光灿烂。我是到后来才发觉,那段时间,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文章里提到父亲,心里始终有一缕凉意缭绕纠缠,文字越来越萧索、晦涩,这让我困惑。入冬之后,我遭遇了今生最冷的一场雪。
十二月的某个早晨,我在市医院的九楼,躲在休息区的窗边抽烟。无数的雪暴虐急躁地从窗口落下去,仿佛我等了一个秋天的答案都在这些雪里。废弃的大烟囱立在雪里,倔强沉默,楼下的平房顶上凌乱、肮脏,雪还没来得及遮盖住这些。许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刚入冬时,有过一场人工增雪,只比霜稍厚些。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又急又重,天地间充塞着它们它们划出的线条,纷繁凌乱。
给母亲打电话:下雪了,很大,不用过来送饭了,我在外面买点就成了。重症监护室的铁门紧锁着,红灯一闪一闪。
头顶落着雪,脚下踩着雪,却感觉不出寒意。从这栋楼到那栋楼,从这一层到那一层,推着父亲做各种各样的检查、拿各种各样的单子、按照吩咐买各种各样的护理用品、换了一个又一个科室,机械而麻木。有种看不见的、沉重的东西在心里越来越明显。医生开出了长长的一溜病因,十几种,说是相互影响相互纠缠。我说我不懂这些,就想问有多大希望。医生说,不到百分之五。
心向下坠了一下,其实还是不相信他的话。那个老人,尽管有好几次把自己走丢;尽管有时候搞不清大小便的地方;尽管常常颠三倒四地讲些从前的事情,但无论如可,很难把他和那个词联系起来。我以为有些事情上,总该会有些例外和奇迹的。
这次住院病他安静了许多,很少去拔扎在手上的针头,也不再和护士顶嘴。更多的时候只是在沉睡,呼吸声粗重,醒来的间歇喂他喝水,还是像从前那样急切,还是会呛到自己。
在他失智的这几年里,我们拌了无数回嘴,每次都以我被气得头疼为止,我很难想像这样精准敏捷的回怼来自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人。母亲在旁边笑着说:你以为我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他是个严厉、强硬的男人,年轻时嗜酒,和酒友起过无数次口角;也因为工作的事情和领导硬顶,吃过一些暗亏。在那些贫乏、荒凉的年代里,来自于他的温情同样稀缺,对我们的教育,打骂居多,很少有耐心细细讲道理。在他渐渐衰老的这几年,我们的角色慢慢对调了。我会像训孩子一样训他,他会像一个不听话的孩子,要么顶嘴,要么一声不吭。其实他不知道,每次我壮着胆子训他的时候,都在担心,他会突然没了痴呆的毛病,给我来一顿狠的。
他经历过最艰难的日子,一讲起“六零年”,讲起他饿死的父亲和小妹妹就落泪。对那些从未见过的亲人,我很难有和他相同的感触。
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艰难。关于童年,我最清晰的记忆是冬天生不起炉子,我们睡的房子屋顶和墙壁的相交处一圈惨白的霜,每天夜里,总要等母亲上炕焐热了被子,我和兄弟才急急忙忙脱衣服上炕。有一年新抹了炕泥没有干透,我们在呛人的烟雾里入睡,半夜醒来全部浑身发软,起不来,动不了。我们边挣扎,边呕吐,最后是我弟弟挣扎着慢慢爬到门边开了门通风。只差一点点,我们就没有这后来许多年的时光。
这侥幸捡来的许多年时光里,他用生硬粗暴的态度带着我们跌跌撞撞的行走,居然也渐渐过得有模有样。许多年后的一个除夕,我和兄弟对饮,酒酣后谈起过往的艰辛,禁不住潸然。这时候父亲已经戒酒许多年,大约也不能完全理解我们在说些什么,见我们望向他,笑得安宁而满足。
去年秋天同兄弟带他和母亲看胡杨,漫天漫地的金黄里,他斑驳的发色格外萧瑟。推着轮椅下一道缓坡时,我对他说,老爸,我要松手了,咱们试下看轮椅能滑多远。他呵呵地笑出声来说,你不想要你老子了就试。
同样的笑容还有过一次。那时候的他退休不久,晚饭后在一起看电视,他突然长长的叹了口气。问他怎么了,他回答的具体内容我忘了,大意是关于死亡的忧惧。我故意用一种不耐烦的口气说,二三十年以后的事,你瞎担的什么心?他突然就开心起来,呵呵的笑。
许多时候我想,对老年人来,痴呆未尝不是一种福利。三分清醒,七分痴呆,可以忘了对于死亡的大恐惧。这一点上,父亲的痴呆应该是幸运的。
在陪伴他的这些年里,看着他不可挽回地慢慢衰弱、老去,许多时候,甚至会让自己生出一种愤怒的情绪来——因为这一切的发生,我都无能为力,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病房里很温暖,他昏迷着,像睡在一场长长的梦里,呼吸声在氧气面罩里又重又长。松开束缚带,握着他的手,防止他无意识的乱动造成滚针。他的头顶上方许多仪器闪动着蓝的绿的光,生命就这样简单地被那些我看不懂的数据和线条标示出来。
雪下得时断时续,在走出医院买饭的间隙,偶尔抬头望天,总是灰的,那些看不清来路的雪无休无止地落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在这样的天气里冻住了,好长时间记不起我出来要做什么。
甚至,我想不起那个病床上一刻比一刻衰弱的老人,他为我做过什么,他对我的意义。我似乎只凭着动物的本能,奔波在2018年岁末的大雪之中,心里的那一点点希望,微弱、黯淡,摇摇欲坠。
又过了两天还是三天,他清醒过来的时间越来越短。母亲说,儿子,把你爸接回家吧。眼睛突然就酸了,带着些恳求的意味,我说不回家。她沉默着,不再说起这个话题。然后挨个给亲戚打电话,让他们来医院看看,又交待他们给乡下的老屋打扫卫生、生炉子,还不忘提醒下雪路滑,行走注意——住院时我们没有通知过任何人——这个时候我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似乎全然没有用处,我还是许多年前那个无措的孩子,看着她沉静地安排这一切。心里深处还是觉得,不至于到这个程度。
我终于没有等来那个微弱的希望,到现在我还是记不起那天是几号。撤去了仪器,取掉了乱七八糟的电线和各种原本不属于他身体的东西,父亲显得清爽、安宁。我把脸贴上他的额头,感受他最后的温度。我很奇怪自己没有悲伤。
不庄严,不悲伤,仿佛这只是2018年一个平常的凌晨。
压低声音,叫着父亲的灵魂回家。却又想起我习惯坐在沙发上写点东西,父亲总在我左手边的靠背椅上,在阳光里打盹。醒来的间隙,总会叫着我的名字,说要回家。有时候我会逗着他,问他回哪儿;有时候不理他,直到他发火骂人。有一回我闲得无聊,问他多大了,名字叫啥。他张了半天嘴,说是忘了。
这样的日子应该无休无止继续下去的。好多时候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忘了许多事情的父亲,却从来没有忘记过我的名字。
出殡的那天凌晨,格外寒冷。不知道是守灵的困意,还是迎送吊唁的客人积攒的疲累,脑子里像有许多念头,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棺木的棱角硌得背上钝疼,我索性坐下来,靠着棺木挪来挪去,总是找不到一个舒服的角度和位置。
毕竟不是怀抱。
我记不起小时候他抱我的情形了,从有记忆起,他很少对我有亲昵的举动。唯有一次,是上初二时,班里一个女同学偷偷给我递纸条,约我第二天在上学的路上见面。偏偏那天晚上他喝了点酒,躺在炕头,摸着我的头发和我聊天,枕着我熨出线条的裤子。我担心裤子被压出折,却又不敢说出来。第二天早上,他把我送到门口的马路上。于是,我就这样错过了我的第一次约会。
陪着他的最后一段路,一路冰雪。突然想起那段青春的、生机勃勃的往事,这是不适宜的。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起这些,想起他难得一见的柔软,却无意中干涉了我一段青涩的过往。这样的干涉和纠缠充满我们的生命,有时候的单向的,有时候又是互相的,到最终,我们已经分不清彼此了。
在他住院前的那个秋天,我写过一篇关于北山的文章,徒劳地想要叙述出生命里难以言表的荒凉。送他到达北山之后,仍旧是我说不清楚的苍白和荒寒,广大而空阔。砂土落上他棺木的声音那么生硬突兀,就像这个世界的某一块被撕裂了,出现了一种无可替代不能言说的空缺。我终于忍不住背转身体。
朝阳初起,天地荒凉,我泪流满面。
自此之后,我将不再完整。
雪停了,世界还要寒冷很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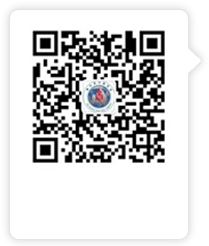





最新评论
点击刷新加载更多